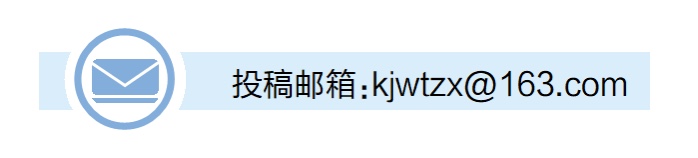近日,重庆市作协创作大会召开,近百位作家共话重庆文学的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的火热实践为文学提供了丰厚的创作土壤和表现空间。近年来,我市作家满怀热忱描写新重庆,重庆文学持续进步、不断突破,在书写中国气派、重庆韵味的文学高质量发展之路上成绩斐然。
要大步向前,也需沉淀和回望。本期《两江潮》,我们特地约请了我市文学领域的4位写作者,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留下一路走来的感悟与思考。
——编者
一
我喜欢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的一句诗:“通过绿色枝条催开花朵的力,也催开我的绿色年华。”——我看到了对日常生活最诗意的表达。
诗人就是能看到生活粗糙的皮肤之下欢快的血液和坚硬的骨头的人,是能够穿过时间的河面看到水流与河床相互摩擦、包容、交谈、握别的人。
其实,我是难以从人群中辨别出诗人的:身边有以写诗为业的人,有以写诗为乐的人,有默默写诗然后随手扔进抽屉的人,有单纯以诗的眼光阅世而不落笔墨的人。诗歌让人善良,读诗、写诗皆然。
我不知道诗意在什么年代第一次出现在人类的大脑中。很确定的是,中国人在三千多年前就有了诗歌这种文学样式,开始了有诗意的生活。
我理解的诗歌是关乎心灵的,它是人类表达心灵的手段。它跟音乐、美术一样需要天资,也跟音乐、美术一样需要技术的训练。并且,诗歌是非功利的,它无法市场化。诗歌如果有用,它的有用性体现在心灵与心灵之间的默契和由此带来的善之上。
诗歌需要独自面对自己,诗歌最终说来是自言自语的另一种方式,它可能更有条理,更符合逻辑,符合阅读者对诗歌的期待和评论家对诗歌的定义,但它终究只是写作者在匆忙一生中的一次次驻足停留,终究只是他写在云上的心灵记录。
那么,诗歌需要被阅读吗?需要,就像人与人之间需要在迎面路过时露出一些浅笑,就像两个相同色系的心灵需要在偶遇时轻轻拥抱,并在各自的衣衫之上留下对方的色泽。
二
汉语诗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复兴时,“抒情”是被作为“前卫”的对手对待的,那时提倡的是“反抒情”。40年后的今天,当我想起“反抒情”时,发现诗歌中已经没有多少“情”可以激起诗人们的兴趣了。
但我是不相信三千年汉诗的抒情传统会这么不堪一击的。“前卫”“先锋”“现代性”这些词,是身体外涂抹的彩绘,一洗就消退了;剩在身体里面的血,才是诗歌的核。每个时代的“前卫”在下一个时代都可能被当作陈词滥调,而一以贯之传承下去的核,才是诗歌的本质。我认为这个本质是抒情。我们可以洗掉身体外的彩绘,但不能换掉我们的血。
从北方的《诗经》到南方的《楚辞》,从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到长短句,再到自由诗,诗歌没有停止过形式的出新。甚至连承载诗歌的汉语也一直在变化中,一个时代的现代汉语会是下一个时代的古代汉语,一个时代的口语会是下一个时代的雅言。传承不变的内核是抒情,这是我们读一首郑风和读一首新诗会同样产生感动的原因。
如果我们回望三千多年的诗歌生活,我们会忽略那些在当时看来石破天惊的“破”和“立”,它们在三千多年的时间流动中日益变得微不足道。诗歌的内核一直在,一直让这样一种文体保持着它的一致性和独立性。
当然,每一个时代都在给“抒情”增加新的内涵,正因为如此,抒情不老。我热爱那些被日常生活感动的诗人,我热爱那些能被他们的感动而感动的诗歌。
三
诗歌如何在一个时代留下痕迹?诗歌不像史书那样记录历史事件,不像小说那样再现社会生活,但是诗歌同样会在时代的身体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诗歌是时代的云彩在湖心的投影,让云彩更加立体;诗歌是时代的声浪与水波的共振,让声浪更加丰满。诗人不可能回避时代的风卷云舒,他需要面对时代,朝生活里走,他能选择的是一个好的角度进入生活,和一种好的语言方式从生活里出来。
回望中华几千年文明史,我们发现诗歌从来没有缺席。那些伟大的诗歌已经成为民族心理中最明亮、最柔软、最敏感的部分,那些伟大的诗行滋养这个民族,让这个民族的灵魂丰沛,让这个民族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生生不息。
我们这一代诗人有责任接续几千年的诗歌传统,为未来留下我们时代的心灵史,为未来的心灵传下不输前人诗歌的养料。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副主任,重庆新诗学会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