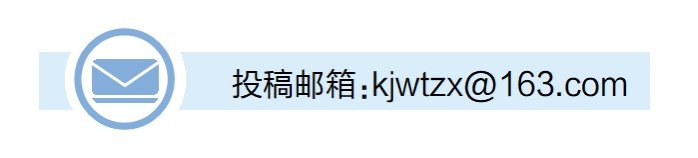四面的山卌形的水。
每每走出四川盆地,对人介绍家乡我用的就是这句话,自认为是我们川渝人对乡情的眷念。进出巴蜀,确实离不开这些山和水,尤其是古代天上没有飞机飞的时候。
巴蜀的古代交通名称,最著名的当源于《三国志》所谓蜀道,经过李白歌咏,天下尽知。
蜀道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蜀道是指逶迤秦巴山区的金牛道、褒斜道、荔枝道、陈仓道之类,百步九折,猿猱咨嗟。广义的蜀道,是指进出整个四川盆地的道路,也是砯崖转石,湍瀑喧豗。还有就是巴蜀内部的通道也可以称为蜀道,地陷盆地,恰与四围泾渭。
先秦汉唐的古人,在盆地内主打的蜀道不是陆路,而是“行走”在若干江河构成的水路上,大部分河道,即使有滩礁、湍流的惊险,却带来轻松出行的得意。
众人理解道路的“道”时,都会条件反射跳跃为陆道。其实,古人出行,转山转岭,必以水行为主。水能载舟,舟能承物。物重陆行,汗蒸如雨;物重船行,轻舟如箭。
重庆学者蓝勇考证,今天名声大噪的“东大路”直到唐代也了无踪迹。即使到了宋代,成都、重庆之间,也只有永川区老牛尾铺村的“牛尾驿”有唯一一个驿站记载,它还是水陆并举,宋代诗人张孝芳《昌州》一诗中,有“发舟马头岸,驻车牛尾驿”便知端倪。
盆地内部奔涌的河流,是以长江东西向干流为经,南北向支流为纬,一北一南的支流,几乎垂直交汇在川江这条干流上,很像一个卌字。由此产生巴蜀历史上较为罕见的庞大水路循环交通网。
从长江北面汇入,依西到东分别是外水岷江、中水沱江、内水涪江、西汉水嘉陵江,构建出卌字的上部。
卌字的下部,就是众多南面来汇的支流。从长江上游到下游,横江、南广河、长宁河、永宁河、赤水河、綦江、乌江等,像长江所蓄的胡须,须尾都在云贵高原飘呀飘的。还有一条特别的酉水河,古代被称为五溪之一,没在胡须之列,但是也斜长在长江脸上。
卌字水网,舟运繁忙,长年有100多种木船船型,或牵挽上溯,或自在飞驶,船名千奇百怪,诸如中元棒、歪屁股、麻雀尾、黄瓜皮、歪脑壳等等。据统计,清末重庆唐家沱进出的木船就多达18000多艘,往来涪江有5000多艘,泸州港平时停泊达3000多艘。
水载舟,舟载物,每条河流都是古代的一条“国道级”通道,古今名声卓著的当属赤水河支流。
汉武帝派唐蒙溯河通夜郎,出使队伍庞大达“食重万余人”。何以比张骞出使西域的二百多人多出了50倍?细究起来,就是物资运输,他把巫山、云阳等地出产的食盐,运去“厚赐”缺盐的夜郎。赤水河当有强大运力,才能承担如此庞大的物资运输任务。
北来南来,向东向西的巴蜀河流,犹如人身上的血管网络,在巴蜀大地交联互通,战争时期调兵运粮更是快捷如飞、规模宏大。
卌形蜀道既是争战之道,物运之道,更是风月之道。长江主流、支流,都有文化故事满满流淌。
李商隐“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就隐隐给我们道出了一条围绕水道的故事,相思辗转却抵不住秋日水涨,无船返家。乘舟水上,春风惬意,古代文人墨客无不高吟,李白“千里江陵一日还”,大唱川江下游舟乘快速;明代蜀中唯一状元杨慎从嘉州到叙州,“好似乘风列子游”,从上游补白一句,沁人心脾,味道大出。
墨客骚人的题咏,可以让一座城市鲜味氤氲,成都、重庆自不必说,单说小小奉节,在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打头下,李白、王维、刘禹锡、李贺、苏轼、陆游等齐齐呐喊,一发力就把一座“中华诗城”的名头吹拂得开花开朵。
“一只兰船当驿路,百层石磴上州门”,白居易任忠州(忠县)刺史吟过的佳句,无出其右地把巴蜀沿江一带城市的诗、水、山串联,把巴蜀的山城、江城、铁城串联。“天生重庆,铁打泸州”,这句民间谚语,道不尽川渝人民的先天禀赋,道不尽川渝大地的血脉悠悠,更道不尽川渝卌字水网馥润的关关雎鸠。
有如忠县、奉节,巴蜀水道路网结出一颗颗璀璨的城市明珠,先秦两汉的城邑,基本上都位于水路之滨。巴国都邑,先后有江州、垫江(合川)、平都(丰都)、枳、阆中,全是傍水而生。
浩浩长江赴沧海,船去船来自不停。卌形蜀道古老,更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