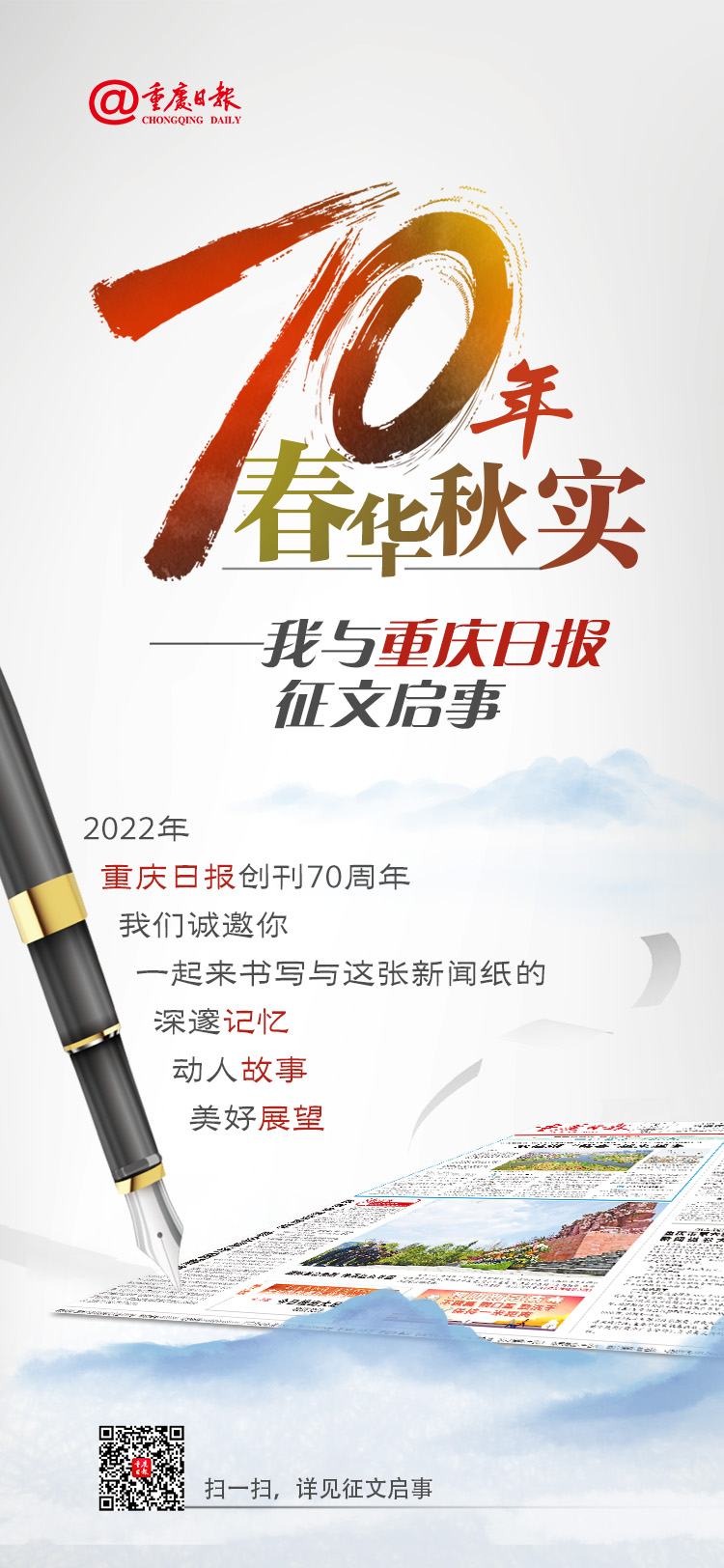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人生梦想,我的梦想就是当一名记者,当一名有成就感的记者。
《重庆日报》帮我圆了这个梦!
《重庆日报》圆了我的记者梦
50年前,我就有了一个记者梦。
1971年7月,初中毕业后的我,没能继续上学,回乡当了农民,拿起锄头“修地球”。
那个年代全国都掀起“农业学大寨”的热潮,我家乡的生产队在学大寨中,也组织了一支改土基建队,将一片坡地改成梯田。有一天,市里的记者来采访这坡地改梯田。在采访现场的一位村民事后对我说:“这记者好厉害哟,把手放在裤包里就把采访的事记下来了。”

▲罗成友(右一)在田间地头采访。
“要是我能当上一名记者就好了!”读书时偏爱作文的我,听了这位村民的话后,对记者产生了一种崇拜之情,有了当记者的梦想。
1978年10月,我因在生产队里种蘑菇,并掌握了制蘑菇菌种的技术,被当时的巴县青木关区多种经营办公室聘为蘑菇技术员。到了区里,有条件读到办公室订的《重庆日报》等报纸后,喜欢写作文的我,便开始照着报纸副刊上刊登的文章,学着写文学作品。经过两三年的坚持,我终于在《重庆日报》副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抓团鱼的小伙子》。
而开始写新闻稿,则是与我的工作相关。
1982年,我在一个小木箱里,用细木粉作原料试种香菇成功。我把这长出香菇的木箱抱到镇上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2寸的黑白照片,然后又按照《重庆日报》上消息的写法,写了一篇《我市人工试种香菇成功》的新闻稿,连同照片一起寄给了《重庆日报》。三天后,《重庆日报》就在二版的左下角,将稿子和照片刊登了出来。
当我看到自己写的第一篇新闻稿上了《重庆日报》后,更激起了我的记者梦。从那以后,我就结合本职工作进行采访,利用晚上和节假日写稿,不断地为《重庆日报》投稿,并成为了《重庆日报》的一名通讯员。
成为《重庆日报》的通讯员后,有机会参加报社组织的一些新闻写作的活动,报社的老师也常来青木关,带着我采访,使我的新闻写作水平得以迅速的提升,写出的稿子,在《重庆日报》《重庆日报农村版》上被采用的频率也高了起来。在当《重庆日报》通讯员的10余年间,我几乎每年都要在日报和农村版上刊发几十篇稿子,还写出了《厂耻鞋》《何志刚卖鱼有“三怪”》《老子服了儿子》等10余篇获得四川省好新闻奖、重庆市好新闻奖一等奖、全国广播好新闻奖的作品,并多次被《重庆日报》评为优秀通讯员。
1993年12月,《重庆日报》在基层通讯员中选调记者,已40岁的我有幸被选中。经过《重庆日报》10余年的培养,我终于圆了做了20余年的记者梦。
《重庆日报》圆了我的“田坎记者”梦
成为《重庆日报》的记者后,因为一次采访,又让我做起了要当一名“田坎记者”的梦。
1994年春节前,报社农村报安排我们几位记者,到农村看一看农民准备如何过年。我到綦江县古南镇的一个村里采访时,见到一位15岁的小妹妹还不知道重庆人过年必吃的汤圆是啥样,70多岁的老母和50多岁的儿子还睡在同一张用木棒绑的床上、靠一个老南瓜过年的贫困状况后,写了一篇《贫困农民的“年”》在农村报上刊登,随即引来了“解放40多年了,咋会还有这样贫穷的地方”的惊讶。

▲“田坎记者”罗成友。
这惊讶让我意识到:农村不仅还有极端贫困,还存在新闻报道的“贫困”,农村还是社会关注的“盲区”。我是一位从农民、农村基层干部成长起来的记者,理应用手中的笔,为农业农村、为乡亲们鼓与呼。于是,我又有了当一名“田坎记者”的梦想。
对我要当“田坎记者”的梦想,报社为我创造了条件,并尽可能地给予支持。在记者岗位安排上,报社尊重我的意愿,让我长期跑“三农”。
有了报社的支持,我也坚持跑农村,跑田坎,专心关注“三农”问题,并写出了一批影响较大、受到广泛关注的报道。
小时候饿过肚子的我,对粮食安全问题特别关注。每年的春耕生产时节,我都会到田坎上去采访,对春耕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农民对当地政府和农业部门如何帮助搞好春耕生产的期盼等,进行及时的报道。这些报道引起了农业部门,甚至市里分管农业农村工作领导的重视。
2002年,我到田坎上调研后,发现农村出现了忽视粮食生产的问题,于是写了一篇《粮食生产松不得》的述评文章。中宣部阅评组看到这篇文章后,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全国重视的问题;2007年5月,我在田坎上调研时发现,耕地撂荒现象较为严重,于是,写了一篇《我市耕地撂荒现象值得重视》的文章,见报后,又引起中宣部阅评组的重视,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也在报道上作出批示,要求市农业部门对耕地撂荒问题进行调查,拿出解决办法。
农村贫困,也是我极为关注的。1994年10月,我到当时重庆市的省级贫困县潼南的贫困村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后,写出一组调研报道,首次较为系统地报道了我市的扶贫攻坚(当时国家正在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需要面对的难题,提出加快扶贫工作的建议;重庆直辖后,我把渝东北、渝东南的贫困区县跑了个遍,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组又一组的扶贫攻坚调研报道。
1999年元旦刚过,我与时任《重庆日报》总编助理张小良一起,用了3天的时间,走进了全市最贫困的巫山县庙堂乡,经过几天的采访调研,写出的《穷乡庙堂纪事》内参稿。市扶贫办一位领导流着眼泪读完,几位市领导批示,要求重点扶持庙堂乡的扶贫攻坚。
在报社的支持下,我坚持跑田坎,写“三农”,圆了“田坎记者”的梦,成为在全国第一位被称为“田坎记者”的记者。
《重庆日报》圆了我的“长江奖”梦
范长江新闻奖(现已合并为长江韬奋奖),是中国记者的最高荣誉奖,这是每一个有点新闻理想的记者都会追求的梦想。作为有记者梦的我,当然也有期望获得“长江奖”的梦想。是《重庆日报》帮我圆了这个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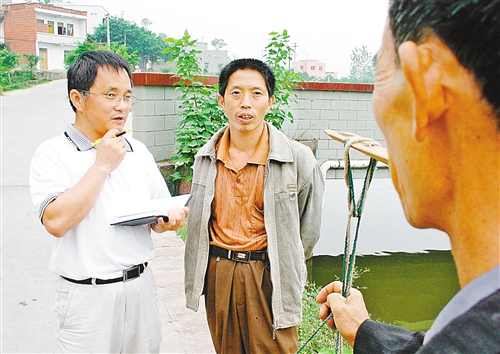
▲罗成友(左一)现场采访。
刚到《重庆日报》作专业记者后,就听不少同事谈起范长江新闻奖,而且还有人开始申报这个奖。当时,我虽然不敢有申报的奢想,但也暗暗在努力,争取有一天能圆这个梦。
《重庆日报》为记者实现这一梦想提供了平台。我知道,要实现这个梦想,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日报这个平台上,拿出够得上获奖的“硬货”来。因此,我沉下心来,钻心干好记者工作。
“长江奖”是记者的最高荣誉奖,唯有在记者岗位上做出成绩,才有获奖的机会。因此,我先后多次委婉地拒绝了报社提拔我当部门主任的好意,坚持留在“三农”记者的岗位上。
“长江奖”首先得有过硬的新闻业务本领,因此,我坚持打牢自己的理论根基,坚持到最基层采访,坚持研究“三农”问题,力争拿出好的新闻作品。
除在农业、脱贫等报道上下功夫外,重庆直辖后,我也特别关注三峡移民,从1997年到2003年三峡水库135米蓄水这7年间,我每年都用10天以上的时间,深入到重庆库区进行调研采访,写出一组深度报道;对粮食安全、耕地保护、脱贫攻坚,乡村治理更是持续关注,所写的不少稿件,先后获得中国新闻奖、三峡大江截流好新闻一等奖、全国省级党报好新闻一等奖、重庆新闻奖一等奖等奖项;我到开县麻柳乡进行深入调研后所写的报道见报后,得到时任市委书记黄镇东的批示,报道总结出的“八步工作法”,被市里作为农村工作法在全市进行推广;2007年,我所采写的有关粮食安全、承包地流转等稿件见报后,三次得到时任市委书记汪洋的批示。
在《重庆日报》这个平台上,只要自己肯努力,就会有回报。2004年,报社推荐我参加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的评选,最终我以评委总票数第二获奖,成为重庆新闻界首位“长江奖”获得者。
《重庆日报》这一平台,不仅圆了我的记者梦,还圆了我的“田坎记者”梦,圆了“长江奖”的梦。
主编:兰世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