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从野蛮生长到鲁奖茅奖,乔叶:回头一看,我居然走了这么远
2024-08-01 18:48
七月下旬,溽暑蒸人,在一年中最热的日子,乔叶又一次来到了重庆。她已经记不太清,这是第几次造访这座山水相拥的西南城市。但之前来过的每一次,重庆留在她记忆里的,都是美好的样子。
是重庆让她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文学里的南方叙事。长江浩浩汤汤,嘉陵江闪着金光,两江交汇之处,从泾渭分明,到缠绵交融,大江大河,奔涌向东,摄人心魄的自然之力,她惊叹不已。
大江成为她跟重庆缘分的起点。那一年,她也是第一次乘坐江轮,经由三峡水路溯江而上,沿途游玩,最后登陆朝天门,开启了对重庆的感知。对于生长在豫北平原农村的她而言,这趟旅行刷新了自己的人生经验。
“在我的老家,土地是大块大块的平原,‘水’的元素很少。”她盛赞,重庆是被江水滋润的地方,“大江大河就是人们的生活日常,而且与我所见到的中原大地上的黄河不太一样,在两岸耸峙的夹缝中,展现出一种恣肆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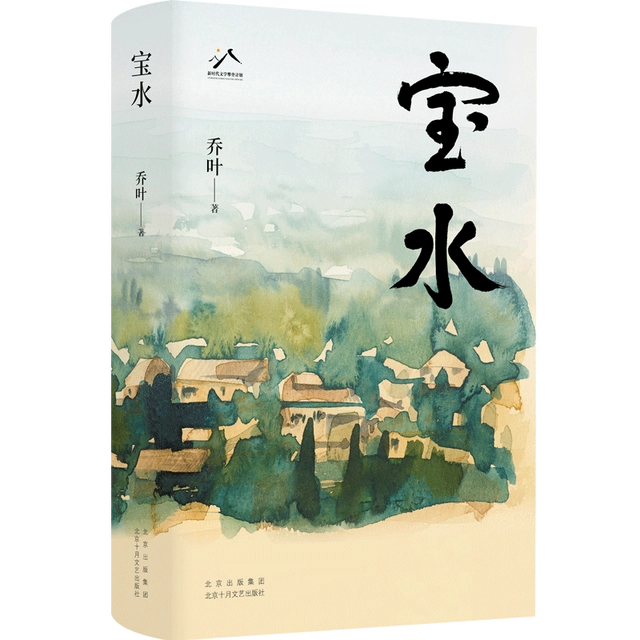
“水”,也为乔叶带来了高光。在2023年夏天揭晓的最新一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乔叶以乡土题材长篇小说《宝水》摘得殊荣,成为70后女作家获得茅奖的第一人。时隔一年,乔叶以新晋茅奖得主身份再次造访重庆。
行程很满。7月28日-30日连续三天,乔叶要穿梭于重庆的三个角落,跟喜爱她的读者见面。酷暑下的连日奔波,很难说是令人愉悦的工作。但乔叶始终神采奕奕,每一个场合,她总是笑意盈盈,声音轻轻,毫无保留地分享对文学的感悟,诚恳耐心地回答文学同行和热心读者所有的提问。

▲7月28日,杨家坪九龙书城,第11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乔叶读者见面会现场,乔叶正在分享。记者 谢智强 摄
“我很爱我的读者,我挺愿意参加分享的,因为我能看到活生生的读者,读者也看到了活生生的我。”她说。
《宝水》出版于2022年底,讲述了太行山深处的宝水村由传统型乡村转变为以文旅为特色的新型乡村,生机和活力重新焕发的故事。塑造了女主人公地青萍、德高望重的老人九奶、村支书大英等多个个性鲜明的角色。
正如茅盾文学奖授奖辞所言,《宝水》映照着“山乡巨变”,“涵容着传统中国深厚绵延的伦常智慧和新时代方生方长、朝气蓬勃的新观念、新情感、新经验在创造新生活的实践和人的精神成长中,构造融汇传统与现代、内心与外在的艺术形态,为乡土书写打开了新的空间。”
乔叶不止一次笑着解释,《宝水》与乡村振兴的“遇见”是个美丽的偶然。“就我个人的初衷而言,其实就是想写历史背景下活生生的这些人。每个村庄都有它的历史,我希望写出历史或者文化的纵深感。”
她希望自己笔下的宝水村是一个中间样本,“它不多先进也不多落后,不多富裕也不多贫穷,它可能是居于中间状态的,符合更大多数的乡村样本。”这个样本,根源于她从小撒欢的豫北乡村,寄托着她对故乡的回望。
“我挺喜欢一句话,叫‘宝水如镜,照见此心’。这颗心不单是我一个人的,可能是从我这里出发能够抵达很多读者的。我希望这部《宝水》可以照出大家的心境。”她承认,年轻的时候,很不愿意自己的文字里透出鲜明的乡土气,“但多年过去,在生活和文学的教育中悄然回首,我对自己乡村之子的身份愈发认同,我的创作也在不断地往乡土回归。”

▲乔叶正在分享。记者 谢智强 摄
乔叶说,自己的文学之路,是从早年乡村生活的野蛮生长中走出来的。
持续30余年的写作,让她从乡村一路到县城、省城,再到如今的京城,让她陆续摘得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多个国家级大奖。
“回头一看,我居然走了这么远。不可思议。地理上逐渐远离乡村,反而在情感上给了我更多动力,以文学的方式不断回望故乡。”做客重庆的最后一夜,乔叶在酒店的房间,接受了记者独家专访。
1、再谈获奖
新重庆-重庆日报:获得茅奖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现在回想,您怎么看待这次获奖?
乔叶:我觉得这个事情挺厉害的。倒不是说我自己多厉害,而是茅奖的社会影响真的厉害。好多以前可能并没有关注我的人因为茅奖关注到我,挺神奇的。
挺有意思的是,因为得了茅奖,也会有人翻出我二三十年前写的小散文或者很烂的小说,甚至最早写过的诗歌,来批评我。其实啊,我在写作上确实不是天才型的。我可能是一个资质平平的作家,有一点点才华,靠着努力和热爱走了这么多年。所以请允许我有个成长的过程。而且我相信自己也还在不断成长。茅奖的确是很重要的奖项,但它不是终点,我还在继续努力,写出更好的作品。
新重庆-重庆日报:这一年来,外界对茅奖的关注会影响到您的生活和写作吗?如何守护内心的平静?
乔叶:哎呀,最大的影响就是这一年来都在接受采访,社会活动剧增,完全把沉浸式写作的时间打碎了。
对于获奖这件事情,我一开始就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就得奖了呢?当时10人提名的名单公布时日子比较难熬,因为总有朋友来讨论这件事,但结果又是未知的。我就想这事儿赶快过去吧,不管得不得奖这事要赶快结束,不然必须面对外界的各种声音,内心不平静,会焦虑。
怎么忽略这些声音?写东西,我开启了一个新小说,把注意力集中在小说上。所以茅奖正式公布那天我还在家写小说,央视采访我,问我当时在干嘛,我说我在写作,特别美好,我正在写作的时候,得到了关于写作的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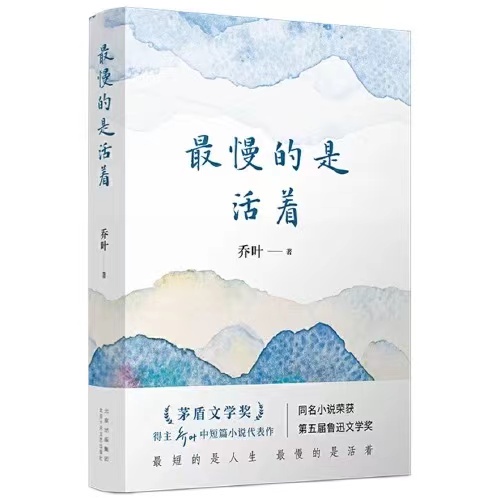
新重庆-重庆日报:您以散文成名,2004年从零起步学写小说,2010年凭《最慢的是活着》拿鲁奖,2023年凭《宝水》获茅奖,短短20年您在小说创作之路上不断飞跃,为什么?
乔叶:首先请允许我自我表扬一下,我的确比较努力,对写作有执着的热爱。另外我确实很幸运,从写作之初开始,得到很多正向的鼓励。我还在中师上学时就开始投稿,而且基本都是一投就中,毕业当老师,成了我们当地《焦作日报》副刊的常客。是《焦作日报》的老师建议我投外面的大报。199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我的《别同情我》,我得以被全国青年报刊编辑看见,稿约源源不断。其实当时的写作还很稚嫩,我自己都不太好意思再看。
后来调到河南省文学院,我开始和李佩甫、李洱等写小说的前辈打交道,因为之前没有经典文学阅读经验,大家的话语体系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谈论文学的态度都让我陌生。我那时在小说界是小透明,我就到处凑过去听老师们谈小说,还缠着李洱老师开书单。我可爱凑着听了,在学习上我挺厚脸皮的。2004年被推荐上鲁迅文学院,那时我想,争取五年之内在《人民文学》发个中短篇吧,结果当年就实现了。
我觉得我先天底子还行吧,比较敏感,充满好奇,算是有些微的小才华,但不觉得有大才华,我对写作充满了热情,渴望。我希望写东西,手写我心,打开自己内心的世界,把我所认知的世界呈现给读者,也很幸运得到了积极反馈,这些都在不断给我很大的动力。外面的光和我内心的光,合照在一起,就成了很大的能量。
当然,我实际上还是有积累的,写小说前我写了十几年散文,所以很多朋友说我进入小说非常快,我想是散文底子打得厚的结果。我在写小说之前出了七八本散文集,更重要的可能是我很爱学习,一直在写作中学习和成长。
2、文学成长
新重庆-重庆日报:早年的乡村生活给了您怎样的文学滋养?
乔叶:小时候我既不漂亮,也说不上灵巧,我特别爱玩,昏天黑地满大街跑,满世界田野里跑,爬树偷枣,看见什么都新鲜,很调皮。村里孩子都这样,放学了就去打草喂猪。我早期的学习过程完全是野蛮生长,没读过什么像样的书,读报纸副刊就是最有营养的了。直到快20岁的时候才读到《简爱》,那是我读的第一本外国文学经典,我很震惊,居然可以这样表达爱情。
如果说有文学的启蒙,那要归功于我奶奶。我是奶奶带大的,她活到了2001年,八十多岁,她去世6年后我写了《最慢的是活着》。后来我反复确认,觉得奶奶是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根本出发点。当初写《最慢的是活着》的时候,我哭过很多次,直到现在,每次想起她还是想哭,奶奶对我的意义,是我逐步认识出来的。
我的作品中很多我奶奶的影子,包括《宝水》,我给青萍的奶奶起名王玉兰。事实上,我奶奶就叫王玉兰,小名迎春。我奶奶没有上过学,只参加过扫盲班粗识几个字。但她懂很多朴素而深刻的道理,有一种强大的民间智慧。她给了我一种很重要的“生命的教育”。后来我去了外面很多地方,见到很多人,经历了很多事,长了很多见识。但我奶奶给我的“生命的教育”,还不断在我内心发酵,成为写作的重要来源,成为文学的营养体。想到奶奶,我会感慨生活就是大浪淘沙,淘出了金子一样的东西。

▲乔叶在村里。
新重庆-重庆日报:野蛮生长的状态之下,您那时是如何通过写作,在心里开出了一朵朵的花?
乔叶:可能内心还是有很热烈的很充沛的东西想要表达吧。我师范毕业还不到18岁,在乡下教书,课又不是那么多,内心又有很多话要说,就写稿。我那时是苦闷和孤独的,我太年轻,不懂得学生的心思。我可能当老师很差劲,一是心理上不成熟。一想到教的孩子永远这么小但我却会慢慢变老,就很难开心。二是很不喜欢重复性极强的工作,也不自律,而教书就是个重复性和自律性极强的工作。所以我选择写作,来纾解心中的苦闷。
写什么呢?一开始完全是写自己那点儿小事儿,比如发愁嫁不出去,我写了《愁嫁》,还写了《一个女孩的自知之明》等等,都是年轻女儿的小心思。(记者: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吗?)不啊,是真的愁啊!挺真诚地发愁,我那时候也没有成家,长得也不行,其貌不扬,脾气有一点古怪,没有感情生活,而且对感情生活莫名绝望,担心在乡下找不到好对象。《愁嫁》就类似于征婚,我看到报刊有征婚启事,一问要花钱登,我想干嘛花钱,我就写一篇稿子,既能挣稿费还能征婚。所以我从开始写作就是手写我心,写真实的东西。
其实一开始我也不自信,这就得说到乔叶这个笔名。乔叶是我第一次投稿时取的,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投的,居然中了。那时编辑部还会退稿,如果我用本名就会退给我本人,我很怕退稿,退回来我觉得很丢人,所以取个笔名乔叶。如果退给乔叶,退到我们班,我是知道的呀,但我假装不认识她,我不去拿。哈哈,是有点小心思,我完全没想到一投就中了,还有稿费寄过来,4块钱,我一直没取,就留着当纪念了。
新重庆-重庆日报:您那时完成的散文温暖治愈且影响极广,却被认为是“鸡汤”,您怎么看?
乔叶:哈哈,鸡汤也挺好的呀。比如《读者》杂志在那个年代为什么特别风行,我觉得是跟时代情绪契合的,那时大家都很努力上进,《读者》里的文章为人们带来了温暖治愈。真鸡汤不可怕,我那天还跟朋友说鸡汤挺好,为什么呢,真鸡汤熬出来是有营养的,鸡汤炖的时候,这个炖的过程也充满了煎熬和痛苦,一番历练才能炖出美味。有火的考验和煎熬,才能炖出真正好鸡汤。
新重庆-重庆日报:说实话,很少有作家能像您这样,从素人投稿时期就一路顺风顺水。
乔叶:可能一开始发稿子很惊喜,慢慢地我就感觉事情就该这样,发稿子很自然,哈哈。后来才知道自己确实很幸运,当然我非常感谢一路遇到的编辑老师,我那一点点才华真的就是这样被一次次鼓励过来的。
但也有不好。就是大家比较宠你,就没有人来指出问题,问题都是自己察觉出来的。我记得有一次,编辑很委婉地告诉我,版面不够,你要改一改,把3000字压缩到2000字行不行,我就压了压,竟然发现2000字比3000字效果要好,于是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个问题了,我怎么写了1000字的废话?我也意识到编辑不会直接批评我,那如果我自己也意识不到问题的话,就很可怕了。所以后来我自己很注重修改。
新重庆-重庆日报:没人来指出您的写作有什么问题,靠着自己的反思,其实也是一种文学上的野蛮生长。
乔叶:对,靠自己反思,自己去悟。因为编辑不明说,只希望我压缩一下字数,当时压倒2000字时我以为改不动了,他说还希望压一压,我又努力压倒1500字,这才实在改不动了。
我慢慢体会到,人与人之间大多还是比较含蓄的。这意味着我要更自律,要给自己把关,文责自负,很轻浮写的东西发表了,被别人看到,再也收不回来。要爱惜自己的羽毛,“文责自负”这四个字特别沉重。
3、回望故乡
新重庆-重庆日报:您在河南一个小村庄长大,文学之路也是从河南起步,《宝水》承载了您对河南故乡的回望。
乔叶:是的,我在茅奖颁奖典礼上就说过,作为一个乡村之子,30年里,对于故乡,我有渐渐远离又徐徐回归的漫长过程。这个漫长过程让我认识到,无论身在何方,故乡的土地和土气,都如影随形地拥抱着我,是我命中注定的精神基因和心灵滋养。故乡拥抱着我,时代也拥抱着故乡。我一直认为,作家和时代就是浪花和大海、庄稼和土地的关系。弱水三千取一瓢饮,这一瓢饮里必然是时代的成分。《宝水》就是我取到的这一瓢水。
我还说过,写作《宝水》耗尽了我所有的乡村生活经验,既包括青少年时期,也包括为写作跑村、泡村这些年的新收获。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从乡村来到县城、又到省城,再到如今的京城,三十多年来,我在地理上越来越远离乡村,远离故乡,但反而在情感上有了更多动力,以文学的方式不断回望乡村。我想,表面上我在“失去”故乡,但却在某种意义上说,我用文字不断地将失去的故乡重新“建造”了出来。

▲7月29日,沙坪坝区重庆大学,学生们专心听乔叶的分享。记者 刘力 摄
新重庆-重庆日报:离开故乡,不断告别,从乡村一路走到京城的过程,也是您一次次主动跳出舒适圈的自我挑战。
乔叶:绝对是一次次打破舒适圈。当老师时,如果我安于乡间生活,算是很不错了,体制内当老师,工作体面,收入不错,人家给你介绍的对象都是乡镇干部,你还想要啥自行车啊对不对?但我不甘心一眼就看到底的日子,我还这么年轻,生活就这样了吗?我不愿意,还是想有更多可能。在县城工作时,我已经是县文联副主席了,决定要去省里。朋友劝我说,你到省里还不知道怎么样呢,留下来挺好的,大小是个县里的干部了。但我还是一次次离开,我反正还年轻,出去看一看又能怎样?
新重庆-重庆日报:这是一种不甘心,还是说您有“野心”?
乔叶:好像也称不上是野心,也不觉得是多大冒险。而且打破舒适圈带给我的一直是很积极的东西,从乡里到县里到省里,我都蛮乐观的,不恐惧。
当然,我一定是不安分的,不安于那种一眼看到头的生活,总想着是不是有别的可能性。后来我从散文转向小说,也是因为小说让我看到了更多可能。从一个小的地方不断地打破舒适圈到更广袤的世界,在更广袤的世界接受更有才华的一批人的潜移默化,自己也得到了不断提升。
我往前走的时候肯定也觉得不容易,但回过头一看,我居然走了这么远,我觉得自己还是挺可以的。
新重庆-重庆日报:走了这么远再回看,故乡很可能已经不一样了,会遗憾吗?
乔叶:没有啊,就是因为不一样我才会去写。对于故乡,我不想写牧歌式抒情,炊烟袅袅之类的,散文来抒情是可以的,但小说就不行。我也不想悲歌式批判。
我也怀旧,让我怀旧的是人。比如小时候的土房子,我肯定不会住了吧,但想起当年住那里的奶奶,我会很怀念,会愿意回到她身边。灵魂还是在人身上,我现在提起老家还是很有感情的,哪怕老人都去世了,但他们埋在那里,意味着亲人还在那里。我有个朋友是山西人,但他从小到大没在山西生活,等到年过半百了才头一次回山西,见到了爷爷的坟,他立马就跪下磕头。这是人与故乡在血缘上的力量。小说就是要写人,写时代变化中的人,要紧贴着人物,人的心跳、情感和温度。
新重庆-重庆日报:您离开故乡是为了探寻更多可能,但现在的部分青年人好像缺乏“探寻”的动力了。也有越来越多人期待回到故乡,回到乡村,但他们倾向于一种“躺平”的人生。
乔叶:我觉得对于所谓探寻要有多维理解,探寻的对象只能是世俗意义的成功吗,不见得。我认为要有一个自洽的标准,探寻的,应该是一个人对待生活状态的满意度。自洽很关键,只要自己活着舒服自我认可就好,这种探寻就是值得的。
我当时为什么一路出走,就是因为不舒服啊,未知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不舒服,那就想要改变它。对于舒不舒服的感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答案显然不一样。
我们不评判“躺平”,但有一点很重要,永远保持求知欲和好奇心。对生活是如此,对写作,更是如此。
凡注明来源重庆日报的作品,版权均属重庆日报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重庆日报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除来源署名为重庆日报稿件外,其他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


























 渝公网安备 50011202500747号
渝公网安备 50011202500747号